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大巴山老家,县教育局管事的对我说:县城中学装不下人啦,你去区里吧;区上管事的对我说:区里装不下人啦,你去乡里吧;乡中学校长对我说:这儿装不下语文老师啦,你去教政治吧。
我想抓个石头朝那些人扔过去:咱中文系高材生呢,又不是劳教对象?念着老母亲没人照顾,忍。我把石头装在心里。
那是一所深藏在山峦里的普通农村中学,我的新“家”,安放在校内一幢地主大楼的二楼。草丛中,裹满蜘蛛网的地主楼像个睡死了的黑莽汉,人小心翼翼地走在里面,生怕惊醒了它被吓着。上楼梯时,得用手顶开一块横盖着的木板。一人走路,整个老楼的地板都咚咚叫。危房。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喝闷酒,啜泣声破窗而出,惊飞楼下的蝙蝠,蝙蝠幸灾乐祸呱叫,又串起池塘里的青蛙一起闹。隔壁女教师气冲冲地敲着板墙嚷道:黑灯瞎火的你整啥呢?人家白居易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你却弄出个大鬼小鬼闹学堂,告你。
上课头一天,我刚迈进教室,就被门上埋伏的一把扫帚掉下来砸在头上,成语“灰头土脸”好像说的就是这种事。才讲几分钟,我就从孩子们茫然的眸子里看到一句老话:读望天书。被我揪着耳朵站起来的班长启升,望着窗外飞过的麻雀说:听不懂呀,老师。
我也听不懂自己讲的什么。我打小政治课都没考及格过,那时的初中政治课,没有像样的教学大纲,主要讲精神文明,也暂没纳入升学考试。我煞有其事地耗着,孩子们也煞有其事地耗着,一如地主庄园里老樟树和狗尾巴草各自野蛮生长,互不张望。
扛了半个月,我发现几个死娃娃又在鬼头鬼脑嘀咕什么,看见我后哼着山歌散开了,带头大哥就是城里来的插班生斌斌。估计斌斌们下回伺候我的,就不是扫帚而是别的玩意了,或者干脆众人拾柴火焰高,把我丢进池塘里去,和猪儿一起游泳。
救救自己,救救孩子。我说。我得改变教学方式。
我的“教改”是这样的:每节课的末尾,都拨出十五分钟开小灶——讲故事。我读大学时最好的自修课是二战史。我想用自己的拿手戏,拿下这帮企图飞起来吃人的孩子。
第一天,我讲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
犹如倒霉蛋虚竹在山洞遇到无崖子,凭空吸来七十年功夫,活了。虽然只有短短十五分钟,这群长期跟父母蜗居在山凼凼的乡下娃,仿佛换了一个人,他们头一回听说大山之外、时光之远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苏军T34主战坦克、德军梅塞斯密特BF-109战机等新词儿。于是,一场场弥漫着惨烈血腥味的搏杀、巷战,一次次从瓦砾间射出的狙击点杀,一个个咬着敌人喉咙同归于尽的红军战士,以及战后曼斯坦因元帅对战争道义和战役得失的反思……都在群山环抱的这间土疙瘩教室里无声展开,连班上最喜欢给男生递纸条儿的秀芝,都听得张大嘴,似乎要把我讲的东西都吸进去。
我从孩子们兴奋的眼光和我自己的激情讲述里,悟出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可怕,一切都可以挣扎,一切都可以重来。
老校长叼着叶子烟杆儿乌云般飘来,他瞅瞅教室里一脸期待的孩子们,想找出隐形的翅膀,又上上下下打量我:小子,上啥手段啦?
我当然再不会挨扫帚的袭击了,还成了学校的“土豪”:隔三差五,孩子们有的塞给我一块煮熟的腊肉,有的揣来几袋裹着泥土的花生,有的提来一瓶苕酒,要求上晚自习。那年隆冬,大雪纷飞,村庄一片银白,冷得连狗儿都不敢露面。银装素裹的群山中,我女朋友披着雪花从另一所中学步行几十里来看我,一见面她就将冻得通红的手伸进我颈子:“快,弄吃的!”斌斌幽灵般出现了,他双手插进军绿色棉袄的袖筒里,腋下夹着一条烧好的狗腿:“给咱师母炖口汤喝吧。啥,哪来的?嘿嘿……”
这当然是多年前的事了。我记得离开那所学校的头天晚上,启升带人早早用扫帚将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几十支蜡光透出窗外,将麦苗都映得通红。含着泪水,我给孩子们讲了最后一课:攻克柏林……
这些年,我和孩子们都在不同的地方“攻克”生活中的难关,联系少了,但我每每从省城回老家同他们重聚,他们都要让我再讲几个故事,欢闹通宵。他们中,当然没有谁飞起来吃人,且今非昔比——斌斌在重庆读完军校后当了军官,启升成了年轻的文史专家,秀芝在乡下教书经常当模范……
寂静的夏夜,苍穹上日升月落,阴晴更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等一场雨,哪怕是一场无法扯破天幕的小雨,它浸湿的不只是我们的身体,更浸湿我们的心田。于是,心田里便会生长出竹子拔节般的青绿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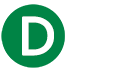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