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终于开了,在这暮春三月,我终于等到了那一树树白雪,那是满树洁净的春呢。
花香是昨晚的雨夜里开始渗进了书房来的,那时我正埋头读着冰心的《樱花赞》,我似乎是从书里就闻到了那一枝枝樱花的芳香,手不禁一阵颤抖,摇摇晃晃地,似乎是春天的影子在我眼前荡来荡去。于是心开始涨潮了,不再像原前的那样安静,我干脆把书搁到了书柜里,不曾想,还未来得及推开窗,竟然就遇见了这美丽的樱花。
花是从窗外将头探进我的书房来的,洁白的花瓣上还流淌着清亮的雨,不,这湿漉漉的花样才更加惹人痛爱。花因为潮湿而愈加饱满,风一来,沉甸甸的花枝左摇右摆,芳香,于是来得更加猛烈了,不一会儿,满屋子都挤满了樱花的味道。
三月暮色,总是那样的深沉,加上雨雾缠裹,这夜,于是浸染了墨一般的黑。夜里,我总是要找点事来做的,总不能白白地虚度了这美好的三月春光。看书,似乎就成了我唯一打发黑夜的方式,一边看书,一边思慕着那早晚都要来的春,心便阔朗了许多去。当然,枕着这三月的夜色看书,实际上阅读的就不仅仅是书了,那里面大抵都还夹杂着一种牵念或期盼的。但是这个三月,我一直没有见到樱花,那一抹抹千丝万缕的牵念和期盼总是缴在心里,闷得人心发痛。
所以,这个三月的每一个白天,我都要去看一眼窗户外的那一岭岭樱花树。每一次,见着它们光洁的枝桠竟然没有半点怀春的意思,心便开始生怨,便恨那晚来的春风软弱无力,连一枝樱花都吹不开。当然,还忧念那瘦弱的樱枝迟迟没有把春的颜色吐在花间,尽管樱花树的枝桠是那么的细小,但这已是三月末梢了,说来,那花是早就应该盛开了。久久地,我站在樱枝下,默默无语,就因为迟迟未有见到那灿烂的樱花,哪怕只是一朵。于是时不时有心灵的疼痛拌和着那些无缘无故地生长出来的哀怨一起疯长,欲哭,却无泪。
都三月了呢,春天早就来临了的,这樱花,迟早都会开的。许多时候,我这样安慰自己,反正,见不着樱花,其他的花到底是可以看见的。我几乎对窗外的那一树树樱枝失去了念想。不过,大多时候,往往见得了那细瘦的樱条儿,亦是会好生心痛的。我想,日夜切切念着的樱花,全是这些瘦弱的樱枝孕育出来的,我不该对它们生恨。我应该拥抱它们,我应该和它们一起等待那片美丽的春色,等待那些婉转又悠远的鸟鸣,等待那不经经典句子意间就遇到了的蝶舞。尽管樱花迟迟没有开放,尽管春光已经落到了三月末梢,总之,已经有一些山鸟,开始了春天的歌唱了,一些蝴蝶,也早早地跳起了春天的舞曲,它们就是春天的信使罢。
这个三月,我常常无边无际地思索着一些与春天和樱花相关或无关的物事,我想起它们,我的泪水就开始泛滥起来。早些时候,也是像这么的一个春天,樱花沉在梦里,很久了,都没有开花的欲念,母亲坐在老屋外的木榄上,望着那一树光秃秃的樱枝,沉吟着:樱花睡过了头,灾难不好求;樱花醒得晚,庄稼要绝产……一遍又一遍,母亲轻轻地唠念着,我还亲眼看见母亲那两池浑浊泪水滑下了脸颊。到底是年纪幼小,不懂事,见到了母亲抽泣,却仍是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语,只会一个劲地往母亲怀里钻。果不然,那年十月,母亲就去了。那个悲痛的时刻只离三月樱花谢尽之后七个月光景而已,虽然此后,母亲不再有疾痛和贫穷,但在我心灵深处,一块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从此开始血流不止。无数次,我反反复复咀嚼着母亲的话,我害怕再次遇见某一个突如其来的三月,看不见樱花的影子我就会伤心落泪。
樱花到底是开了,借着书房里散发出去的灯光,我终于看见它们白灿灿地结了一树。窗户外面的山梁,虽然隐匿在夜色里,但我分明还能辩得出那一岭岭绿色,其中,那灿若星光的白色斑点,一定是樱花。不知不觉间,我感到一股吉祥的瑞气拂向心底,我想起了唐人李商隐的句子: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苍垂扬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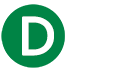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