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鲁迅先生写在他的后院墙外,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时候,我们家屋前的槐树总会一下子窜过来,不过是一株,在屋的左侧。
这株槐究竟有多久的岁月呢?一个大人刚好合抱过来,树阴匝地,覆盖大半个庭院。槐开时节,一簇簇,一串串,花如珍珠,缀满枝头。幽香四溢,挤出院落,弥漫整条胡同,迎向每一个路人的鼻翼。
听父亲讲起,它是差不多和我同岁的。我出生后,父亲在第二年春天就买了一棵槐树苗植下了。后来,我知道了江浙一带有生女儿而植香樟树的习俗,就跑去问父亲为什么不种香樟树。父亲只是笑了笑,淡淡地说,咱们豫东平原可没这习俗,我当时只是觉得槐树好养,也是一种花,而且你一天天长大,大人们忙,刚好可以让它陪着你,不至于太孤单。
的确,我的童年,少年,甚至我前二十年的光阴都是与它密不可分的,点点行行,写满了槐的味道。
最初记起槐的样子,是细瓷碗口粗,枝叶稀疏,花朵寥落,星星点点。不过,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它已经是一种很美的花卉了。在左邻右舍的孩子眼里,那也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成长的过程中,因了这株槐,添了多少乐趣!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槐树下嬉戏,槐树下吃饭,槐树下数星星……且在每一年的春光柔软的下午,常常爱这样玩,一个个伸开小手,用大拇指和食指去丈量槐的胖瘦。年年丈量,年年如此,却不知人在长,槐也在长。
在花的国度里,槐花是最具平民气质的吧,王谢堂前不需要它,百姓家里倒是常见。令人叹服的是它不仅可作观赏,宜可食用,吃起来满口幽香,难以忘怀。在众多的花里,能做得如此体贴周到的也就是槐花了。因此,在过去那吃食不是很丰富的年代,屋前的一树槐花成了最美的期盼。
曾记得,槐花刚展露笑脸时,我已急不可耐,一遍又一遍催父亲搬梯子摘槐花。我站在树下,仰着脸,四月底的阳光洒在脸上。母亲也在树下,拿着小篮,小心翼翼地接摘下的槐花。然后,母亲清洗,拌面,上锅蒸……又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终于可以吃了,一阵香甜的清气萦绕,吸一口,已经醉了。因了这树槐,我们每年在它的花开时节都能享受槐花盛宴。当我长大成人去外地上学后,再也没有赶上过它的花期,可是梦里梦外总缠绕着那甜丝丝的气味。
就像人的一生总会磕磕绊绊一样,槐树的一生也不是那么顺水顺风。翻盖新房子时,父亲犹豫再三,还是把它保留了下来。有一年下大雨,屋子漏了,几位叔伯帮忙检修,上到房顶一看,原来是槐树的枝干茂盛,压破了瓦片,大家都建议把树伐掉,父亲终是舍不得。后来,父亲爬上去,用锯一点点把碍事的枝干锯掉,这才安心。在房屋的左侧是储物棚,父亲每次把那辆机动车推进去都特别费劲,家里人几次三番劝说伐掉,父亲总是无动于衷。
今年的槐花时节,我带着幼子回家看望父母,这是十年之后我再次赶上了它的盛开。傍晚和父母坐在槐树下聊天,槐花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飘落。我突然想到了白居易“薄暮宅门前,槐花深一寸”的诗句,这一寸深里该有多少光阴的故事呀!一寸光阴一寸金,掐指算来,这槐也有近三十年了,它站成了光阴里的风景,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始终不肯伐掉它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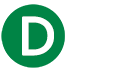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