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老村
我开始学会与老村相互厮守。静静地仰卧在老村旷野。慢慢回想往事,回忆陈年足迹。
用身体的翅翼捕捉草地上的蜂鸟鸣虫,任凭午后的风,撕扯两鬓的斑白。同时,把自己的心事搁浅,找寻一些若有若无的日子。
站在稻香四溢的田野,我向田间的白鹭致意。走在摇摇晃晃的田埂上,我成了陌生人。
回到老屋的檐下,抚摸刚刚出生的小狗。母狗用警惕的眼神怀疑我。它不知道我的来历。
旧的故事,早已完结。新的故事,没有开始。我心中装满记忆,在老村的土地上久久伫立。老槐树有气无力的身体,已无法经受三十年前我鸢飞猴跃的身影。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丝丝地喘着粗气。我臃肿的身材,无法找寻童年的背影。
仰望雨后的村庄,我向天空致意。白云转瞬即逝。连脚上的泥泞也未曾擦掉。老村的日子,不见踪影。
老村印象
诺水河畔的并蒂莲,开了一茬又一茬。船工号子的吼叫,让野茶灞夏日的黄昏阵阵颤栗。
这只是老村年复一年的例行公事。这条河,以及这座村庄的老旧,我已经无法考证。河边的桑园,人来人往。一场洪水,人去鸟散。周而复始,桑园依旧。把老村的夏天折磨得死去活来。
父亲进过桑园,母亲也进过桑园。桑园的秘密依然。在野茶灞,桑园也是一个古老的传奇。
村庄的格局,是秘密也是风水。那些依山傍水的小木屋,吊脚楼,小窝棚,更多保持着历史的痕迹。究竟是明清时代的风月,还是历史风情的蜕变?在缺牙漏齿的水码头,何处寻觅私塾先生的咳嗽声,以及牛肋巴的窗愣?
关于老村,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习俗。公鸡打鸣,也许不是在早晨。女人出嫁,迎亲的还有老丈人。老村事情让人费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就这么过去。
山外一缕清风吹来,老村变得措手不及。就像一个装模作样的读书人,穿着拖鞋,背着行囊。高深莫测的表情,让老村在秋天,也充满寒意。
一个人的还乡
一个人走在星光稀落的旷野上。四周草木茂盛,花朵绽放。村庄悄无声息,像一个慈祥的老人,在等候从乡村散失的孩子。
每一个走出的人,都在盼望归来。正如我一直想回到生我养我的野茶灞。在我出走的日子,村庄默默不语。当我怀揣乡音返回,村庄安详恬静。
电话里的絮絮叨叨。亲人见面的嘘长问短。我的牵挂像一张看不见的网,一直笼罩这个欲罢不能的地方。离开村庄的日子,我就像草木,像尘埃,像没有根的蒲公英。彼此间的问候,或莫名的牵挂,那些和我一道陆陆续续走出村庄的人。
我居住的城市并不遥远。走出村庄我用了三十年的时光。在异乡,我忙于生计,娶妻生子,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多时候,回乡的思绪都停留在想象里。
一个人走在还乡路上。长长短短的牵挂,一如长长短短的思念。在故乡和异乡之间,河水叮咚,昼夜流淌。
把灵魂安妥在故乡。我知道,故乡是我心中永远无法邮寄的书信。字里行间,写满密密麻麻的渴望。
青杠林子
野茶灞的土地,百草丛生,树木丰茂。引人瞩目的却是青杠林子。悬崖峭壁,或丛生,或单挂,或抱团,生长的轨迹,一如既往。
没有青杠不成林。父亲的话,让我想入非非。青杠林子的记忆,令人心伤。三表叔曾误入青杠林,当他满怀欢喜从崖头返回时,被一枝横斜的青杠树枝碰撞。像一架土飞机在山崖上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真是万幸,他最终被崖底青杠树的简单手势,凝固在地狱门口。
父亲用独特的方式,为青杠林打开了一道生命的通道。那些横七竖八的树木,在他乱七八糟的摆布下,悄然生长出神奇的耳贝。这块让村人心悸的地方,从此成为村人发家的秘密。
村庄的日子,被时光拉得老长。青杠林子茂盛依旧。父亲却却与我们阴阳相隔。走过这片青杠林,仿佛走过父亲一生无法解脱的梦魇。
鸟声中的乡愁
头顶的花环。伏手的野草。出没的荆棘。我童年的欢乐,在蚂蚱的跳跃中,一晃而过。
蹦蹦跳跳,四处觅食的小鸟,哪一只是属于我的快乐。很多来不及想象的情节,像初春的芽草,一夜之间从我的笔尖淌过。
人生就像四季牧歌。从春到夏,从秋走进冬。季节把许多姹紫嫣红的故事一一绽放。我捡拾人生的贝壳,却悄悄把怀春的往事珍藏。
在大巴山深处的一个村庄。萧瑟秋风在头顶阵阵掠过。我试图放飞自己满怀的心事,却只看见一些凌乱的秋草,慢慢把头发变黄。
鸟鸣声声。把村庄的年轮一圈圈消瘦。那一缕淡淡的乡愁。随着村旁的河流,汩汩地流向远方。
梳理疲惫的记忆,看见一些散淡的炊烟,有气无力文章阅读地向我招手。不知道,那是不是属于我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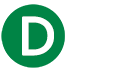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