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上,若要知道什么时候换季,看风就知道了。
风从山坳边远远地吹来,带来了某些秘密和讯息,这些秘密,山水知道,草木知道,庄稼人也知道。
立春过后,往往还是冬寒之际。这时的风,虽没有冬天那般凌厉,但还是有阵阵寒意,也有些任性,它们会在某一个晴天,疯狂摇动村上的一切,枯木树枝也跟着忽东忽西地摇,农人们知道,这是风在摇木水,草木萌动,要发芽了。
我一直认为,木水应念作魔水。你瞧,一夜之间,那些草木,如同魔法般,东边冒出一点,西边冒出一点,稀稀拉拉,若有若无,但却是真的存在。风却还在若无其事般地吹着。这时节,人们还窝在屋里,在这冷风中不敢出门,但草木,却早就行动起来了,直到樱桃的花苞开出来,人们惊呼一声,哟,春来了! 风这时才知道包不住了,于是放缓了步伐,变得轻柔起来。
雨是风最好的润滑剂。几场雨过后,风就变得圆滑起来,它们和庄稼窃窃私语,和草木卿卿我我。庄稼人嗅出了风的不一样,在田间忙活起来,苞谷、水稻、黄豆、南瓜,全都种到地里,让它们自己发芽。这些种子一挨到泥土,就听到风的声音了,一个个攒足了劲,见风就长。风也很高兴,一会摸摸苞谷,一会儿看看南瓜。与它们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想,它们无非就是唠唠那些庄稼的长势,哪一种庄稼该施肥了,哪一种庄稼该起垄了,哪一株植物该开花了。
父亲比风还着急,三天两头地往茶园跑,看看茶叶发了新叶没,迟迟不发叶的茶园让他很担心,是不是年前没有给茶园施足肥、没有修剪好茶枝,耽误了茶叶发新芽。这时的风,总是慢吞吞地飘来飘去,它混在雨里,让人摸不着,看不到。今年的春太迟了,父亲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大口浓酽的茶,他的搪瓷缸里泡的陈茶叶,已让人苦涩不堪,父亲急需要一些新茶,那种清碧的汤色,能让他的女儿们上学无忧,能让他多买几包肥料,再就是,隔壁老王家的小猪崽们长势挺好,他打算要买几头回来。父亲总把自己安排得如同一粒种子般饱满,春种秋收,晴耕雨织。柴米油盐的日子,要一一铺开来。
不久,树梢上冒出了一层新绿,这时的风,如同和煦的阳光,愈加柔软。在某一个晴朗的清晨,风轻轻抖开一缕声音,就拂开了整个村庄的希望。农人们这时可忙坏了,他们在田间像风一样跑来跑去地忙。苞谷营养坨移栽,洋芋苗施肥,谷粒要下秧田,要多忙有多忙,可他们高兴,笑声比风还爽朗,在田野里欢悦无比。
风也在跑,它从这块田里跑到那块田里,偷听女人们的家长里短,偷听男人们的安排打算,偷听圈里的猪呼呼鼾声。一晃,苞谷挂胡子了,南瓜拖着个滚圆身横躺在田里,稻谷佝偻着腰。风一会儿吹过去,一会儿吹过来,满田的绿叶也跟着左右翻飞,那情景,犹如书法家在挥毫泼墨,悬腕挥动,
笔走龙蛇,乱得无章无法,自成一派天书。这应是风最得意的时候了,如同一个沙场点兵的将军,所到之处,万马欢腾。庄稼人立在田里,这一拨接一拨的风,吹得他们通体舒畅,风带来了各种庄稼成熟的气味,果实发酵的气味,这种气味,让农人们欢欣、愉悦,血液沸腾。他们粗糙的手掌甩抹着脸上的汗珠,如同把美好和希望甩给了风,让风带着它们去心中的远方。
风是村庄的魂,任何一株普通的草木,风都能让它们翩翩起舞,风给了它们自由的灵魂,让它们平凡的生命充满诗意。在村庄,狗尾草能开花,稗草能结籽,因为,它们拥有风的呼吸。
庄稼的生命里早已浸透了风的魂。这当儿,各种庄稼已经成熟,它们再也不喜欢跟着风浪漫了,一个个勾头垂腰,挂满了沉甸甸的心思。被风吹大的庄稼,生命里已另有颜色,它们即将离开风,踏上一条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路。即使这条路荆棘遍布,风霜雪雨,它们也将义无反顾。风也内敛了许多,再不像以前那般张扬,它们撵着农人的背篓打杵,轻风细语,与庄稼恋恋不舍地道别。实在不放心,爬上屋顶与树梢上,低低徘徊,如同那老母亲在送别离家的孩子。那渐行渐远的身影,让老母亲从此失了魂,牵挂成在村口年年岁岁的守望。
最后的一片叶子也和风告别了。风从此失去了魂,每天对着空荡荡的村子,它不知道自己要干点什么了。一天到晚从东到西地荡着,丢三落四。还好,它还有村子,村子就是风的家。
风与村子总有说不完的话,村庄如同留守在家的妇人,整日默默无闻操持家务,风却是四季在外闯荡的男人,回来了就给村庄讲着外面的样子,外面的世界,哄得村庄眉开眼笑。当然,风与村庄有时难免有个磕磕碰碰。风总以为自己见多识广,心情不好时,对村庄不屑一顾,对着村庄乱发脾气,独自撇下受尽委屈的村庄。等到风在外面闯累了、受苦了,就会想起村庄的千般好。风又回到村庄,窝在村庄舔着自己的伤痕,对村庄赔着不是。村庄也一如既往地低眉顺眼,与风共享着属于自己的那一私语,日复一日,风把村庄吹老了,村庄也把风看老了。风与村庄的日子,就这样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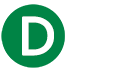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