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足麦一家在这个早晨把夺翁玛贡玛草原都吵醒了。深邃的天空中才有些许亮光撒下来,远山的云层还很倦怠,他家的大儿子大声嚷着:
“这个不要了,城里没用处,拿来做啥啊,那个可以搬走,轻点儿。”
那会儿郎卡正躺在藏床上做一个梦,他梦见自己仰卧夺翁玛贡玛草原,天空很深,也很蓝,太阳却并不像现实中那样耀眼。两只鹰在高空盘旋,缓慢滑翔,他看着它们越飞越高,后来不动了,像被钉在深蓝的天上。他瞪大眼睛,却猛被足麦的大儿子吵醒。郎卡嘟囔着骂了一声,侧过身去用被子蒙住头,足麦家的声音还是从狭小的缝隙里渗透进来,清晰而明确地喧响在被子里。
“快点,大家都快点,搭把手,把这个搬到车上去。”
前一夜,足麦请夺翁玛贡玛草原上的乡亲们去家里喝青稞酒,算是辞别。郎卡不想去,那种离别的场面总有些悲悲戚戚的,看着心里不是味。不过这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各种问题纠缠综合在一块儿,他自己也理不清楚。他让小儿子多吉去足麦家应付,那边不时差人过来,最后足麦在县城里工作的大儿子自己跑来了。
“阿扣郎卡,阿爸念着你呢,去坐会吧,你再不去,阿爸他自己要来了。”
阿扣是藏语里叔叔的意思,他这样说,郎卡不能再待着不动。
他跟着前去,足麦家里坐满了人,看见他来,足麦非常激动,眼中甚至有泪光闪动。足麦招着手,要让他坐在旁边,他却远远地摆着手,坚持在曲学嘎玛身边坐下了。
年青一点的汉子已有酒意,他们唱一段山歌,说一会笑话,把气氛调得非常热闹。笑声不时响起来,像一股浪潮在夺翁玛贡玛草原上四散开去。笑声之中郎卡不时看看足麦,他看见足麦满是皱折的脸上笑容像被机械操控着,大家的笑声响起时,他脸上所有的皱纹就弯曲起来,跟大伙一块儿笑。屋里的笑声弱了,那些皱纹瞬间伸展开,只留下淡淡的忧伤。
一切都不对劲,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又横亘在心里。喝下一碗青稞酒,郎卡没再继续坐下去,他拍了拍曲学嘎玛的手,悄悄离开了。
在被子里,郎卡紧闭双眼,睡眠早已远去,他只是不想清醒。
汽车和摩托的声音一块儿轰响起来了,就在它们即将开动的那时刻,郎卡撩开被子撑起身体。床边就是小方格窗,透过小窗,他看见足麦一家人坐在东风牌卡车里,车箱中装满要搬走的家具,十几辆年青人的摩托车齐声哄鸣,那是送别的队伍。
卡车慢慢启动,开向草原,足麦一家随颠跛的车晃动不停。一些摩托在前面飞驰,还有一些紧跟在卡车后面。年青的骑手都异样地兴奋,他们一手抓住车把,一手放到嘴边,吹响尖啸的口哨,齐声吼着:“啊嘿嘿!”这吼声表达了他们对足麦一家的羡慕,也诉说着他们对未来的心愿。
卧在早晨的牦牛群被这声响惊扰,纷纷站了起来,它们扬着尾巴,默默注视车队在草原中奔驰,并慢慢远去。
郎卡的眼睛一直跟着车队,他看见足麦坐在驾驶坐旁边,足麦巨大的身躯从东风卡车狭小的窗口中探出来,挥舞双臂告别夺翁玛贡玛。随卡车越来越远,他的身体也越探越厉害,整个上半身都挤出了车窗。他保持着这个姿势在草原中渐渐远成了小黑点,郎卡却还依稀看见他的双臂仍在不断挥舞。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足麦告别草原的姿势让郎卡的鼻子瞬间酸起来,眼泪像结了冰花的玻璃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相信把身体探出车窗的足麦也看不清草原的一切,他的脸一定早已湿透。
天更亮了,薄薄的浮云呈现出多种色彩。人虽远去,小山头上煨桑的青烟正不断升腾,没有风,柏枝散发出的烟成一个柱状上升,渐渐散在虚空之中。这是足麦一家在天不见亮时点燃的桑烟,带着祝福和祈祷燃烧。
又一户人家就这样迁走,夺翁玛贡玛只剩下九户牧民。
二
郎卡在送别返回的摩托声中起了床。小儿媳卓嘎端上奶茶,看见他的双眼通红,小声问:“阿爸,怎么了?哪里没舒服?”
郎卡挥了挥手示意没事,他有些害羞,脸也跟着红了起来,忙低下头,不再让她看见发烫的脸和红红的眼睛。
刚把糌粑挼好送进嘴里,前去送别的多吉带着一脸兴奋进了屋,多吉是郎卡最小的儿子。看见郎卡已起床,忍住脸上的表情默默坐到对面喝茶。一碗滚烫的茶喝进肚里,还是没能忍着,畏畏葸葸地说:“阿爸,阿扣足麦一家也走了,我们几时走啊?”
郎卡没有说话,他只是看了看多吉,在他的注视下多吉迅速埋下头去,不敢再提这话。他把手中的糌粑吃完后跨出门去,这是近段时间里养成的习惯,他总在煨桑的山坡上迎接夺翁玛贡玛第一缕阳光。
草原上东风卡车的车辙还很鲜明,青草倒伏着,形成两条泛白的线延伸向远方。
路过足麦家时,郎卡停下了脚步。这是一幢石头垒成的藏式房屋,二楼由横着的圆木架起。此刻,房门洞开,房内空空如野,被搬空的石房显得生硬而冷寂。这些石头如此尖硬、牢固,但有什么用呢?过去在牧场迁徒时,路上总能看见残留的建筑,一样是石房,却早已坍塌,只剩半截参差的残墙勾勒出房屋曾经的基本模样。那时候郎卡常爱猜想这里边住着怎样的一家人呢?他们为什么迁走?是遭遇了重大雪灾?那年月,也只有一场大雪灾可以让牧民流亡,让村庄瓦解。足麦家的房屋多年之后也必将坍塌,最初是二楼横着的圆木慢慢腐烂,长满虫蛀的孔,它们再也承受不了任何压力,在某一天轰然倒塌。那一天的夺翁玛贡玛草原还有牧民吗?轰然倒塌的声音也许只能惊飞几只麻雀,惊跑草地上蛀洞的兔鼠和雪猪。
郎卡无奈地摇了摇头,不愿意再想下去。穿过牛群的时候他遇上了良巴。良巴是藏语疯子的意思,良巴穿着那件陈旧的僧袍,僧袍上布满泛着黑光的油腻和污渍,他盘腿坐在草地上,等待早晨最初的太阳。他眯缝着眼喃喃念诵什么,念叨一会儿,猛然睁开眼,像被惊扰了一般呆呆地看看远方,目光渐虚,失了焦点,只仿佛他凝视的并不是这现实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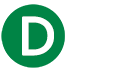

评论0